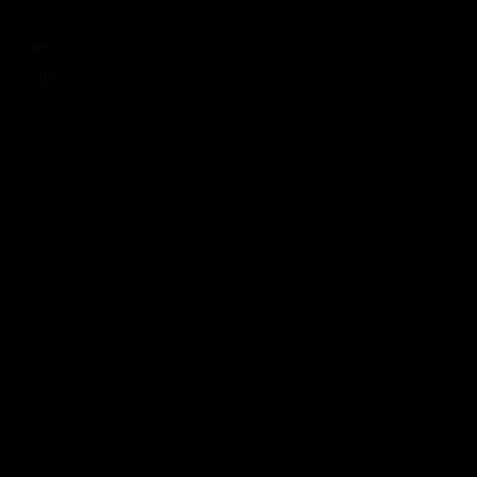中東國家的現代奴隸:黎巴嫩卡法拉制度下的家務移工

黎巴嫩現場採訪、攝影/陳彥婷(獨立記者)
▎接續上篇:《被拋下的幫傭:黎巴嫩戰火下,無處可去的外籍移工》
戰火燃燒逾13個月的黎巴嫩,終於迎來停火。曾經繁華的土地上,除了居民,還有一群長期被忽視的人,苦痛鮮少有人聽見。移工、性小眾——被社會邊緣化的身影,從未真正融入主流,在戰爭陰影下成為最無助的存在。當炮火擱置,所謂「和平」是否只屬於某些人的平靜?獨立記者陳彥婷走進被遺忘的角落,記錄在真主黨與以色列戰爭中遭遇滅頂之災的移工與性小眾。戰爭結束了,但社會的裂痕未必痊癒。遺落在時代縫隙的弱勢群體,如何在未來的黎巴嫩找到一席之地?
「假如我沒有登上那班飛機,我的命運會不會改寫?」這個問題,或許是Myra過去20年來,不斷在她心中盤旋的迷思。
原本生活安逸的她,在菲律賓曾是有執照的護士,日子平穩無憂。她能流利地講英語,和許多志向遠大的年輕人一樣,Myra也渴望新的挑戰。2004年,她決定放下已有的安穩生活,嘗試在加拿大尋求護士職位的機會。命運似乎總是充滿意外,一次會面中,仲介向她推薦一個出乎意料的選擇:有個黎巴嫩的家庭需要一名私人看護,條件不錯,還能擁有些許私人時間和不錯的薪水。Myra猶豫再三,最終踏上了前往中東的航班。
然而,現實與想像大相逕庭。「我確實成為了那個5歲男童的私人看護,照顧他患有癲癇症的病情,但工作內容遠不止此。」Myra笑著回憶,語氣中夾雜一些無奈。「我不僅要照顧他,還要幫忙打理家中的大小事,做飯、打掃、洗衣,簡單來說,我變成了一名家庭幫傭。」
由專業看護變成普通家傭,那時的她並不甘心,但也無奈接受了這個現實。從打掃、做飯、洗衣服等家事她都唯唯諾諾,試著將這份工作盡可能做到最好,「直到有一次,我的女主人要求我打掃陽台,而我有懼高症。當我向她解釋時,她竟然回我說:『所以妳覺得我們是請妳來讓你摔死嗎?』」
黎巴嫩約有13.5萬名移工,大部分來自衣索比亞、孟加拉、獅子山共和國、斯里蘭卡和菲律賓。大多數移工是女性,她們受雇到私人住宅做家務工作,包括打掃、煮飯和照顧雇主的孩子。連同家庭幫傭的外來移工只能應用唯一的合法制度——卡法拉制度(Kafala),雇主作為移工的擔保人和贊助者,負責申請移工的工作簽證,同時可決定合約條款和工作條件,令移工更容易受到剝削和虐待,甚至走入人口販賣圈套。
不少家庭幫僱的經歷中,雇主會沒收他們的護照與簽證文件,令他們無法中止合約或離境。此外,不少雇主訂下苛刻的工作條款,例如永遠把移工鎖在家内、沒有雇主陪同不可外出;休息日不定時,或者可能一個月只有一天;有些移工沒有自己休息的房間,要與雇主的孩子同睡、睡走廊、睡廚房、睡陽台等,有移工支出,有人曾8年都沒有放假,有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黎巴嫩哪個地區工作,有的甚至沒有電話卡。

27歲的Suward本來在獅子山共和國開時裝店,生活不俗,但她為了子女未來,打算把生意擴展,當時時裝店月收入只有150美元,她被到海外當僱員月薪350美元的優厚薪資吸引。從抵達的那一刻起,她被載往一個家庭作幫傭,這是夢魘的開始。沒收電話、護照,呼喝她做家事⋯⋯她不諳阿拉伯文,女主人很強勢,她只能唯命是從。有一次,雇主要求她處理水煙,Suward因健康原因沒有完成工作,對方便對她拳打腳踢,成為她在黎巴嫩遭遇暴力的開始。
黎巴嫩美國大學2022年報告中曾指出,68%家務幫傭受到一定程度的性騷擾,11%受到性侵犯。無國界醫生指出在2022年,近1500名幫傭因為工作或居住環境,深陷憂鬱、焦慮或創傷困擾,需要接受輔導。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在2008年調查,每一周就有一名幫傭不自然地死亡,多為自殺。
幫傭死亡的另一項原因是嘗試逃跑,在艱難處境之下,不少移工只能選擇逃跑,但除了承受被抓的風險之外,雇主也可能控訴移工在家偷竊,來推卸支付移工離境的費用,再來是移工基本上沒辦法取回自己的文件,加上脫離合約,不符合文件要求,可能面臨被羈留、遣返。
畸形的卡法拉制度源於伊斯蘭法律的法律監護人,在20世紀初,因採珠等產業需要外地勞工而在海灣國家興起,本來是引入鄰近國家的阿拉伯工人,但因為憂慮外來的阿拉伯人會在國內傳播另類思想,挑戰海灣國家主權,加上東南亞僱員更便宜,許多雇主在70年代石油業興旺時,開始轉為僱用東南亞國家的非阿拉伯工人。對海灣國家而言,湧入大量移工令人口比例急劇轉變,有些國家50年內人口飆升10倍,為了保障本地雇主,卡法拉制度逐漸演變成雇主極權的制度。
這種「擔保人制度」並非黎巴嫩獨有,沙烏地阿拉伯、約旦、阿曼、卡達、科威特、約旦、巴林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都有,但各國的卡法拉制度稍有不同,例如在黎巴嫩,移工不受勞動法保障,沒有基本合約,換工作、終止合約都必須得到雇主許可。但黎巴嫩的勞動法對於基層工作的家庭幫傭者尤其苛刻,第七條特別剔除他們,讓他們沒有最低工資和工時的保障,沒有定期休息日,也不可參加工會。

相比之下,香港和台灣法規較為重視家務幫傭的基本權益。在香港,幫傭享有最低工資、休息日保障,以及合理的工作時間,又享有《僱傭條例》及《雇員補償條例》等與本地僱員同樣的僱傭權益及保障,台灣也有類似的法規,幫傭每天必須享有總計不少於12小時的休息時間。雖然在執行上仍存在挑戰,尤其是在工作環境的透明度和僱主責任上,但比起幫傭被視為雇主財產的黎巴嫩,仍算是小巫見大巫。
曾在2015年,黎巴嫩的國家聯合勞資工會宣布建立一個家庭幫傭工會,超過200名幫傭響應,國際社會亦支持,但國内聲音卻異常保守。時任勞動部長直指工會違法,斥法律程序足以保障權益,而非把幫傭扯入政治與階級的遊戲,又指外來移工打擊國內競爭力,質疑成立工會只為國際社會的捐款。最終,工會在一片唱衰聲下解散,深化卡法拉在黎巴嫩國内的關係。
黎巴嫩司法機構多年沒有為幫傭權益把關,缺乏投訴機制,執法部門漠視雇主虐待行為早已為人詬病,國際人權組織斥責利害關係人與其他國際組織亦置若罔聞,如歐盟、聯合國等缺乏推行實際措施,加上整個制度涉牽涉價值一億美元的產業鏈,仲介公司便賺取近6成,所以他們明知移工將面對虐待、不合理工作,仍然視若無睹,推動廢除卡法拉制遇上阻力,各國社會也沒有加以打擊。
「仲介不會告訴他們事實,有些人連這邊有戰事也懵然不知。這邊國家用專機把幫傭送走,明天又有新的一批女人來到。」Myra說得特別感慨,因為她自己也是受害者。自從與女雇主的一次爭執,Myra的底線被踐踏,向仲介要求返回菲律賓,但仲介要她自行繳付3,500元美金的手續費,Myra不希望為家裡帶來困擾,最終選擇留在黎巴嫩,並接受成為家庭幫傭的命運。
隨著時間流逝,Myra逐步擺脫卡法拉制度的枷鎖,當過美髮師又轉了行,最終結婚。Myra不僅重獲自由,還與兩位同樣來自菲律賓的朋友Mimi和May共同創立一個支持菲國同胞的團體Tres Maria。「沒有人比起移工,更能夠理解移工的處境。」自知黎巴嫩國內有經濟問題,國內風氣亦不特別積極,Myra便決定自己組團自己救,從疫情期間開始支援在黎巴嫩的菲律賓人,從一開始每星期固定發放米、罐頭食品、日用品等,到後來開始舉辦文化交流活動,又販售手工醬料和手作產品,為當地移工社群提供經濟支援。
「假如我沒有登上那班飛機,我的命運會否被改寫?」Myra依然無法確定問題的答案,但肯定的是,在沙漠中生根發芽的卡法拉制度,束縛無數移工的命運,讓他們的希望如同隨風而逝的沙粒。幫傭要走出困局,跨越到自由,除了依靠當前的國際組織之外,或許只能依賴自己。


責任編輯/王穎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