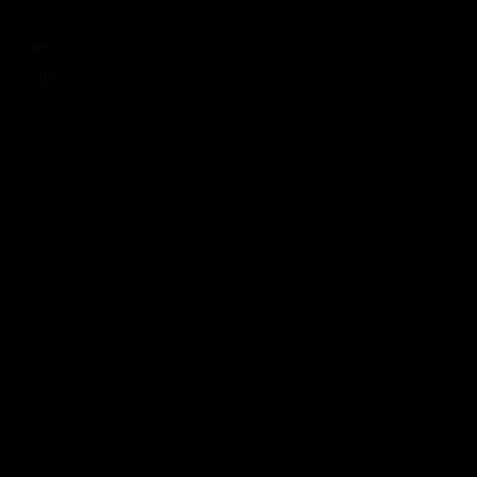被拋下的幫傭:黎巴嫩戰火下,無處可去的外籍移工

黎巴嫩現場採訪、攝影/陳彥婷(獨立記者)
戰火燃燒逾13個月的黎巴嫩,終於迎來停火。曾經繁華的土地上,除了居民,還有一群長期被忽視的人,苦痛鮮少有人聽見。移工、性小眾——被社會邊緣化的身影,從未真正融入主流,在戰爭陰影下成為最無助的存在。當炮火擱置,所謂「和平」是否只屬於某些人的平靜?獨立記者陳彥婷走進被遺忘的角落,記錄在真主黨與以色列戰爭中遭遇滅頂之災的移工與性小眾。戰爭結束了,但社會的裂痕未必痊癒。遺落在時代縫隙的弱勢群體,如何在未來的黎巴嫩找到一席之地?
對於來自非洲、亞洲的移工來說,黎巴嫩是個充滿矛盾的家。這片土地既是生存的機會,也是無法逃脫的深淵。
▌一夜之間,家園成廢墟
Zainab,來自獅子山共和國的27歲移工,正在貝魯特打掃和料理家務。每個清晨,她都被爆炸聲驚醒,那是她在黎巴嫩的新日常。那天早晨當她睜開眼睛,望著手機時間「9月26日,清晨5點」,她原本計劃再睡一會,因為2小時後就得起床打掃、煮飯、洗衣……然而當她再度醒來,平凡的日子卻被無情的現實改變了。
走出房間,Zainab發現雇主和她的家人都消失了,屋裡空無一人。門沒有上鎖,但雇主一家悄然離開,連一紙告別都沒有。她才知道,雇主一家已在深夜離開黎巴嫩,奔向杜拜,希望能夠逃離迫近的戰爭。留下的是未支付的薪水和未曾道別的寂靜。
站在空蕩蕩的家中,Zainab一片茫然。她立刻聯繫姐妹們,但以色列的空襲依然如火如荼地進行中,「幾乎每30分鐘就能聽到一次爆炸。」她焦急地走出大門,決定去找非洲同鄉。貝魯特街頭的混亂情景如同末日,人們成群四散奔逃,驚恐的眼神在空氣中彌漫。
傍晚7點,一顆炮彈就在她距離200公尺處爆炸,碎片劃過她朋友的身體,帶來死亡的陰影。這是Zainab第一次親身感受到,戰爭的距離已經觸手可及。


▌戰爭中的無奈
2023年9月,黎巴嫩的戰爭升級。以色列的炮火從南部擴展到首都貝魯特,猛烈的空襲將真主黨的據點——貝魯特近郊的達拉維夫(Dahieh)夷為平地。貝魯特街上滿是流離失所的民眾。除了黎巴嫩人,還有許多來自非洲、亞洲的移工,原本遠離戰爭的外來者,在戰火中變成無家可歸的難民,包括同樣來自獅子山共和國的Jaiiatu Koroma。
2023年11月來到黎巴嫩時,21歲的Jaiiatu對新生活充滿希望——她來到這裡擔任家庭幫傭,想要幫助家裡度過難關。但當她發現自己懷孕時,這份希望瞬間破滅。她的雇主不但要求她進行墮胎手術,甚至將她無情地趕出家門。仲介強迫她接受手術,她堅決拒絕。隨後,仲介將她扔在了街頭。Jaiiatu依賴國外丈夫微薄的收入勉強度日,當她的兒子Madisha誕生時,她的處境更加艱難。她無法回國,戰爭的陰影讓她深感無助。
當炮火降臨黎巴嫩,Jaiiatu的恐懼達到了頂點。「那些日子,我的神經完全繃緊,因為這不是我的國家,我對這裡一無所知,我根本沒地方可去。」她抱著5個月大的兒子Madisha,在沙灘上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。「我完全不敢睡,擔心寶寶,擔心隨時會有爆炸。」
▌群體的力量:街頭的收容所
在街頭流浪的移工,沮喪、無助的情景被路人拍攝並上傳到社交媒體,迅速在網上傳播。黎巴嫩居民的Lea在貝魯特看到這一切,她心生一念,決定和數名朋友幫助她們尋找收容所。起初,她們在黎北的Tripoli找到一處,但移工們只待了一夜便被趕走,理由是「她們不是黎巴嫩人」。黎巴嫩資源本就緊缺,隨著戰爭爆發,僅有的900個收容所已經爆滿,黎巴嫩人自己都無法得到足夠的庇護,更遑論外來者。
終於,Lea和朋友們在貝魯特市內找到一個廢棄的雪佛蘭工廠作為收容所。那裡四面只有破舊的土牆,但它成了無家可歸的移工的臨時避風港。第一天只有10人,隨著消息擴散,收容所的人數迅速增加,最終達到了200人。
Lea和朋友們動員社會各界捐款,為移工收容所提供床鋪,並分配每個人負責的工作,看到她們不太喜歡捐贈的黎巴嫩菜,便安排她們輪流煮飯、清潔。這批移工從熟悉的味道、語言交流中找到慰藉,一個個移工開始混熟,寂靜無聲的收容所亦增添了音樂與歡笑聲。Lea每天都會花時間與移工交談,聽她們的故事。「一開始,我以為她們都只是被雇主遺棄,後來,當她們開始信任我們,我才知道她們每個人背後都有那麼多的辛酸。」
在收容所裡,牆上一張「尋人啟事」引起了注意,啟事寫著:「你見過她嗎?」這名移工曾被鎖在住所,無法逃離,直到一次空襲奪去了她的生命。Lea又提到另一位移工的故事:她試圖逃離雇主,發現門被反鎖,無處可逃,最後不得不從露台跳下,導致骨折⋯⋯Lea激動地說,「她們每人的故事都可以拍一齣電影,是如此的瘋狂。」
國際移民組織(IOM)曾透露,「我們注意到有些黎巴嫩人在離開住所後,將移工鎖在屋內。」IOM還估計,戰火中有37名移工喪命。黎巴嫩衛生部表示,以色列與真主黨的衝突已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,近1萬3千人受傷。以色列則表示,他們的攻擊主要針對真主黨據點,並事先通知平民撤離。


▌不平等的社會結構
「這只是其中一個收容所,你知道黎巴嫩有多少收容所嗎?大概只有20個,這只是我們知道的。」Lea語氣裡透露出無奈。她見過不少其他收容所,有的設施簡陋,甚至男女共處一室。有一群蘇丹移工也被困在黎巴嫩,因為蘇丹的戰爭,他們成了兩個火場之間的無助亡命者。
「我渴望離開,但我走不了。」這是無數移工的心聲。其他國家的僑民可以通過專機撤離,但這些移工無法逃離,因為她們的護照都被雇主沒收。這正是黎巴嫩根深蒂固的「卡法拉制度」(Kafala)所致。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協會,卡法拉制度將外籍移工的工作和簽證綁定在雇主手中,移工若想換工作或離開,必須徵得雇主同意。未經許可的離開,會讓她們面臨監禁或驅逐的風險。
由於大多數人的護照被雇主扣押,200名移工中只有4人持有護照。Lea與朋友們不辭辛勞地與黎巴嫩當局和國際移民組織交涉,最終爭取到專機,將沒有護照的移工送回家園。坐在一旁的Zainab面有難色,「我是個孤兒,回國也沒有誰在等我。再加上⋯⋯」她拉下褲管,右大腿從骨盆向下有一道10多公分長的疤痕,是她來到黎巴嫩第一份工作時,拖地滑倒,骨盆大腿受挫,術後她無法工作超過1年半,現在走路仍一拐一拐。「我不想回非洲,因為當地醫療系統差,我的腿又未完全康復。」有人疑惑,但也有人歡喜。身為媽媽的Jaiiatu與眾人都鬆一口氣,「我很興奮,因為我的寶寶不需再受苦了。」
這是一次勝利,但Lea也不掩飾她的困惑和悲哀:「坦白說,我每晚都睡得很安穩,因為我活在我所認知的泡沫中。」她感慨道,「我是個白人,生來就處於優勢地位。這就是黎巴嫩,這就是這片土地的潛規則。可悲,但這就是事實。」
「 假如那些流落街頭的人是我,也許有10個人會停下來,但沒有人為這些婦女停下來。當我看到那段影像時,她們已經在沙灘上度過了整整3天。」
Jaiiatu與其他移工最終登上專機離開黎巴嫩時,Zainab也在資助下,得以在黎巴嫩接受手術,修復受傷的腿。Zainab和Jaiiatu的故事只不過是萬千移工身影的一角,這些被邊緣化的群體經歷,不僅是黎巴嫩現代社會的寫照,也是對「人道」與「社會責任」深刻反思的呼喊。在這片充滿矛盾與對立的土地上:誰的生活能被真正看到?誰的痛苦,才值得被世界所聽見?
▎下篇接續:《中東國家的現代奴隸:黎巴嫩卡法拉制度下的家務移工》


責任編輯/王穎芝